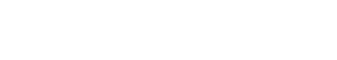我已经快20年没有梦见过他了。
昨夜梦中回到老屋,土墙下的石榴树开得火红,水气氤氲中,外公牵着牛走进雨中......犹如电影场景般在梦中一帧帧反复回放。清晨,我在哽咽中醒来,眼角仍有泪痕。
外公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儿女,我母亲排行第四,是他最小最疼爱的女儿。四个女儿个个善良孝顺,两个儿子学习刻苦,在那个年代先后考取学校毕业分配了工作,吃上了公家饭。父慈子孝,兄友弟恭,乡邻没有不称赞的,我想这很大程度要得益于我外公的悉心教导。
我六岁上学前是和外公外婆一起度过的,那时我的两个小舅舅在外工作尚未成婚。小小的我在外公外婆膝下承欢,为他们带来了很多欢乐。同样,那也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。
童年的印象中,外公辛勤劳作一天后最大的娱乐,就是倚在院子的屋檐下,打开红灯牌收音机,边听单田芳的评书,边给家里的老黄牛打理草料。春天万物萌发,小小人儿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托着大铲子到处搞破坏。外公心疼我力气小,特意给我制作了一把儿童版锄头,这样我就可以轻松挥舞“武器”,一会儿给蒲公英挪个窝,一会儿把土墙边的矮牵牛刨得七零八落。
夏天大雨如注,我坐在屋檐下吃菱角,外公蹲在小板凳前用刀把坚硬的菱角剁开,把果仁挤出放进我的小瓷碗里。老屋房后有一棵大树,每年都结出像杨梅一样的果实来,每到成熟时就会噼里啪啦的掉果子,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果香。傍晚,外婆把晚饭端到院子里,发面饼子和南瓜稀饭,凉拌茄子拌上香油,酸甜的腌蒜头摆在小桌子上。在毛咕咕(一种鸟)的叫声中,我坐在凉床上等着外公回家吃晚饭。
秋天树木凋零,田里的庄稼蔬菜已经收割完毕。土墙根下,我是外公的小助手,抱着一颗颗刚收获的大红萝卜来回奔跑,看着外公把它们像列兵一样埋到沙坑里窖上,这样可以保持萝卜的新鲜爽脆,一直可以吃到过年。成年后,我对植物和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和热爱,而这多半源于童年时期与花草树木、田野山林为伴的农村生活经历。
冬天大雪封门,周围的小山全都被白色笼罩,寒冷的冬天里,我照例是不出门的。早晨起床前,我赖在被窝里像扭麻糖一样,外婆把在火盆上烤得暖呼呼的棉裤棉袄哄着给我穿上。外公坐在火盆边,小铁勺里放上一把玉米粒,看着玉米膨胀炸开花,嘴馋的我往往等不及,偷偷把手伸进火盆去抓,被火燎出水泡来疼得哇哇大哭。
外公疼我爱我至深。我小时候经常咳嗽发烧,每一次生病,老人便整夜守着,喂水喂药。记得有一次我感染了肺炎,农村医疗设施缺乏,外公深夜里背着我,深一脚浅一脚,徒步十几里到县里医院看急诊。外公一生中,在我身上倾注的心血比对自己的子女尤甚。
在外公外婆的呵护下我无忧无虑的长大,六岁的时候父亲接我回家读书。我的离开让外婆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,想我想得快疯魔了。外公怕外婆思念成疾,于是大雨天步行三十多里赶到我家,要接我回去小住几天。父亲怕老人带着孩子路上不放心,坚决不让外公带我走。失望的外公谢绝了母亲的一再挽留,含泪当天冒雨回了家。我母亲每每回忆起外公都会心酸难过,埋怨父亲当时太过固执,说此生唯有此事最对不起他老人家。
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外公病逝了。出殡那天,我只记得院子里纸扎的大白马,那时候还小,不明白生离死别意味着什么,只隐约觉得老屋厢房里再也听不到他病重时的咳嗽声;外公牵着牛走进雨中,再也不会回来了......
如今屋后老树仍在,年年结出红彤彤的果子,老屋已在十多年前推倒重建,外婆也已92岁高龄,子孙满堂。而我亲爱的外公长眠地下已经快30年了,我很想念他。有生之年,抚育之恩已无以为报,清明之际写下这篇小文,聊以为祭。